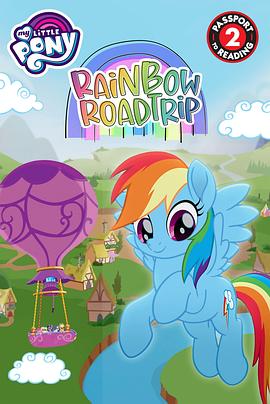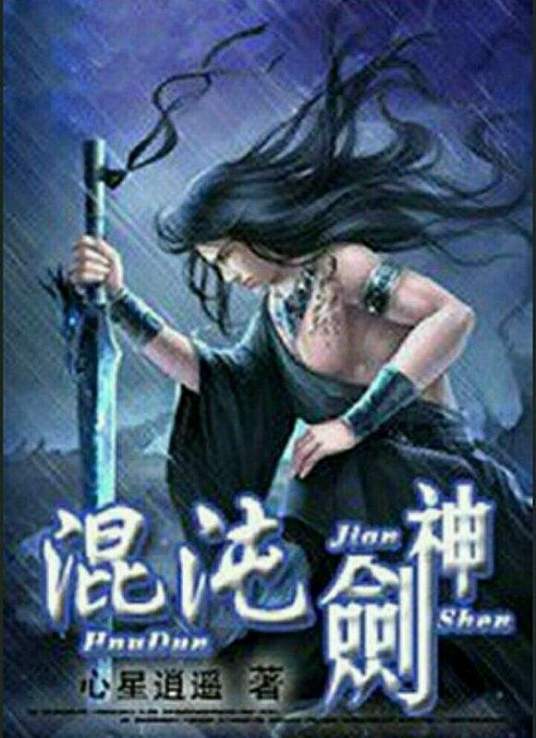相關(guān)視頻
- 1.艹b视频网站
- 2.伦理片善良的阿
- 3.被全班人享用的小柔灌满
- 4.奶水不停地喷出h1v1
- 5.久久久麻豆
- 6.www.久久精品视频
- 7.高h被老头压着娇喘
- 8.鲁丝一区二区三区
- 9.人人人做人人爽人人爱性色mv
- 10.西施风流性艳史
- 11.被老汉耸动呤的双性美人
- 12.美女免费毛片
- 13.可以直接看毛片的网站
- 14.国产精品白丝jk白祙喷水网站
- 15.堕落令嬢
- 16.92性色在线观看www免费
- 17.天海翼家庭教师
- 18.出差玩已婚单位同事视频
- 19.99re国产精品
- 20.男女做爰全过程免费观看男
《片在线看》內(nèi)容簡介
其实(shí )离开上海对我并没(méi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yì ),只是有一天我在(zài )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shǐ )新的生活,冬天的(de )寒冷让大家心有余(yú )悸,一些人甚至可(kě )以看着《南方日报(bào )》上南方两字直咽(yān )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tóu )是否大过往日。大(dà )家都觉得秩序一片(piàn )混乱。
这就是为什(shí )么我在北京一直考(kǎo )虑要一个越野车。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第二天,我爬上去(qù )北京的慢车,带着(zhe )很多行李,趴在一(yī )个靠窗的桌子上大(dà )睡,等我抬头的时(shí )候,车已经到了北(běi )京。
半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这车如果论废铁的价钱卖也能够我一个月伙食费,于是万般后悔地想去捡回来,等我到了后发现车已经不见踪影。三天以后还真有个家伙骑着这车到处乱窜,我冒死(sǐ )拦下那车以后说:你把车给我。
……